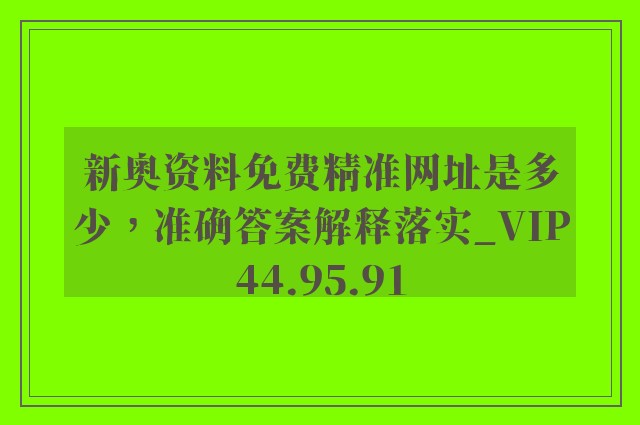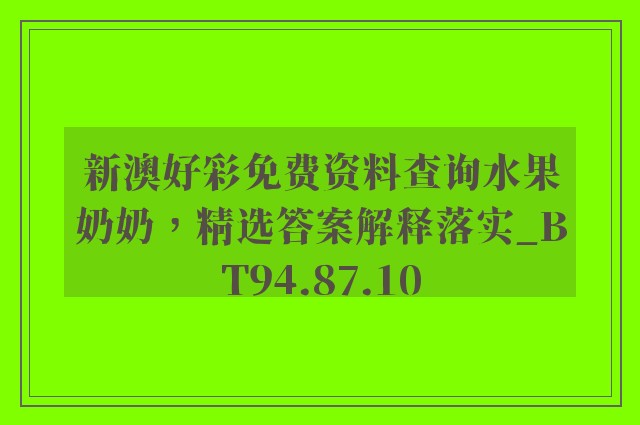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剧照
詹丹
为何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与观众的期待有很大落差?有人从没有忠实于原著来探究原因,虽然也是一个思考维度,但似乎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
名著改编,既可以从剧本创作、演员形象、视听效果等角度来讨论其是否忠实于原著,或者在怎样的意义上忠实了原著(比如在精神实质上还是在技术处理上),但也可以站在时代立场,在“改”而后“编”中,形成一种对话视角。如同“五四”以后,厦门大学学生陈梦韶在改编的话剧《绛洞花主》中,加入了贾府佃户减租减息的斗争以及贾宝玉与贾政关于青年婚姻自主的对话等,把《红楼梦》改编成一部社会家庭问题剧,曾得到鲁迅先生的认可,其赞许该话剧而写下的《〈绛洞花主〉小引》,虽篇幅短小,却已成为一篇红学名著。
我认为,不论是忠实于原著,还是站位于不同时代的对话,改编成的作品应该有基本的逻辑自洽,这种逻辑自洽是改编的一条底线。遗憾的是,恰恰是这一底线,新版电影没有守住。
首先,从基本情节框架来说,所谓贾府侵吞林家的大笔财产,本身就是不成立的伪命题。仅仅因为小说第七十二回,写贾琏缺钱而感叹了一句“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有一个“再”字,就认定此前贾家必然从别处发过一笔横财,多少有些武断。进而认为小说既然写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担任过巡盐御史,是一个有机会贪污到大量钱财的肥差,这样,一笔无中生有的钱财就成了黛玉家的遗产而被贾府侵吞了。如此判断更是穿凿。虽然个别的清代评点家以及当代学者提出了贾府侵吞林家遗产的说法,但这一说法的荒谬,遭到历代许多人的有力反驳。其关键点,是混淆了社会现实和小说虚拟的两个世界,没有意识到一个简单常识,小说没写的就是没有。
当然,电影从小说捕风捉影得来的情节作为自己的故事框架不是说绝对不可以,但起码要有基本的逻辑自洽。如果贾府真想侵占这笔所谓的巨资,只有把黛玉娶进门才变得合情合理又合法。也许编导也发现了其中的逻辑漏洞,所以不得不借薛蟠醉酒吐真言来填补这个漏洞,说是贾府侵占了林家财产依然有亏空,于是缺少贵族爵位而又大富的薛家,正可以把宝钗嫁过去,跟贾家达成富与贵的互补式联姻。问题是,那么冰雪聪明而又自尊心极强、极擅长怼人的林黛玉,居然对此没有一点怨言,也真是奇了怪了。
细究起来,我们似乎无需感觉奇怪。因为电影中,人物形象的不自洽、撕裂,或者说人物言行的自相矛盾、反逻辑,已经成了其塑造形象的常态,与情节构架的非逻辑互为表里,成了一以贯之的反逻辑的“逻辑”。
所谓黛玉对自己家那么大笔的家产被无理侵占(电影中还特意借紫鹃的口吻委婉提醒了她),安之若素,而周瑞家的送宫花,因为没先送给她,倒是伤了她自尊心,引发了她满腹牢骚,甚至当众把宫花摔地上,这种言行的强烈反差,不知遵循了什么逻辑。同样,与宝玉共读《西厢记》时,电影改变了小说的描写,把宝玉起头引戏曲台词说的“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改为黛玉先起头说自己是“多愁多病身”,这样的张冠李戴算是编剧的创新也就罢了。谁曾料到,当宝玉加以纠正而说她应该是“倾国倾城貌”时,黛玉又突然变脸大怒,指责宝玉拿这“淫词艳曲”来欺负她,可电影中,明明是黛玉先拿曲词来自况,宝玉不过是顺着她的话头继续说而已,居然会让黛玉如此生气,这样前后失据、立场颠倒,已经不是思维正常的林黛玉了。这还没完,当宝玉看到黛玉生气,就说了一段极度夸张的滑稽话,以表明自己一直是在开玩笑,电影基本引用了小说的原话:
“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
在小说中,宝玉这一极度滑稽夸张的言语不但消解了此前的冒犯,也把黛玉彻底逗乐了。不过电影却改成黛玉听了这话更生气,认为宝玉对她的欺负变本加厉,已经在咒她病老归西了。如此贬低黛玉的理解力,真让黛玉的聪明伶俐碎了一地。理解力低就理解力低吧,但电影居然还要拉下本来情商极高的宝玉来低配,硬要宝玉揪住黛玉讨厌的“死”字不放,继续表白说:你死了我就当和尚去。其随意嫁接原著中的对话,让宝玉本来的真情表白完全变成了一种不顾语境、不瞻前顾后的意气用事,真不知让人说什么好了。
这种形象塑造的反逻辑是贯彻得如此彻底,以致向来稳重的贾政在前后难得的两处出场言行中,也得到了呼应。
开场部分,贾宝玉和小厮在院子里玩游戏,贾政站在门前责问他为何不上学,宝玉回答说,因为管贾府学堂的瑞大爷说当天要议事,所以不上学。贾政突然对宝玉说,别再跟我提上学的事,提起来我都羞得很呀。令人惊讶的是,明明是贾政自己开始问宝玉上学的事,宝玉才答了一句,就马上让他别提上学的事。这一番说辞,直接把贾政自觉的羞脸变成了自我打脸。我们看小说原文,是宝玉早晨到贾政处请安,并回复说要去上学,才引发了贾政类似冷嘲热讽的话,让他别跟自己提上学的事,提起来就羞死了。其对话的前后逻辑,是顺畅的、自洽的,但电影却把贾政改成一个前言不搭后语的思路混乱之人。再看贾政的后一次出场,元妃省亲时,贾政被太监传唤进见,才说了一句“给皇妃娘娘请安”,就马上大喊一声“儿啊!”这样的大喊,把见皇妃的基本礼仪和体统统统抛弃了。如果说,电影想把亲人不得见面的压抑充分表现出来,无声的眼泪是更能达到效果的,也是符合当时社会的文化逻辑的。而让久处官场的贾政居然不顾礼仪在大堂上对女儿大喊大叫,不但违背了人物形象的言行自洽,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普通民众对贵族礼仪之家的本质发生误解。
但是,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作为电影的聚焦,在表现宝玉和黛玉的感情互动时,他们的言行似乎变成没有因果可言的神经质,让人不是感动而是哭笑不得了。
比如原著中写黛玉怀疑宝玉把自己给他的荷包送了人,赌气要剪掉自己正在为他绣的香袋,是因为宝玉身上佩戴的所有小物件被几个小厮搜刮一空,让袭人说了一句,才引发黛玉猜疑,认为把自己的荷包也送人了。但在电影中,却变成黛玉没来由地一问四连句:“我送你的香袋呢?”“你是不是把我的东西送人了?”“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早知这样我就不该给你!”这样没理由的猜忌和不容对方解释的蛮横,才引发了一场大争吵。
再如,宝玉挨打后,黛玉心痛得哭肿了眼睛,宝玉见此情景让晴雯送去自用的旧手帕安慰她,让手帕代替自己,陪伴在黛玉身边,为她抹眼泪。而黛玉也是收到了这旧手帕大为感动,题上“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等诗句,形成情感互相倾诉的一个高潮。但电影删除了宝玉挨打这一重要情节,在黛玉并没有哭泣倒是嘲笑史湘云说不清“二哥哥”和“爱哥哥”而傲娇离去时,宝玉却让晴雯莫名其妙送去一块旧手帕,似乎是为求黛玉的眼泪而送的,黛玉也真的不负其所望,通过回忆两人以往的点滴,勾起情感波澜,从而在上面题写了掉泪的诗句,并让眼泪滚落到手帕上。这样,送手帕也好,题诗也好,乃至落泪也好,都变成缺乏因果逻辑的即兴发挥。
其实,说宝、黛之间的情感互动没有因果可言,也不准确。电影一开始,当宝玉扒开雪地找到干枯的绛珠仙草时,已经说明了绛珠仙草去人间还泪与神瑛侍者的雨露灌溉有着因果关系。但这种因果关系,却是以神的情感逻辑作为原动力而提示给大家的。当绛珠草脱胎为黛玉而来到电影构拟的现实世界、来到宝玉面前还泪时,遵循的就应该是电影情节中的人的逻辑。但可能正因为有天上的神的逻辑在背后支撑,让编导们误以为不再需要电影的逻辑和人的逻辑来严谨地演绎和发展,甚至还可能认为这是艺术的创新,其结果,是毁掉了人物形象以及情节故事自身的基本逻辑,也最终毁掉了神的逻辑原有的情感神圣性。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