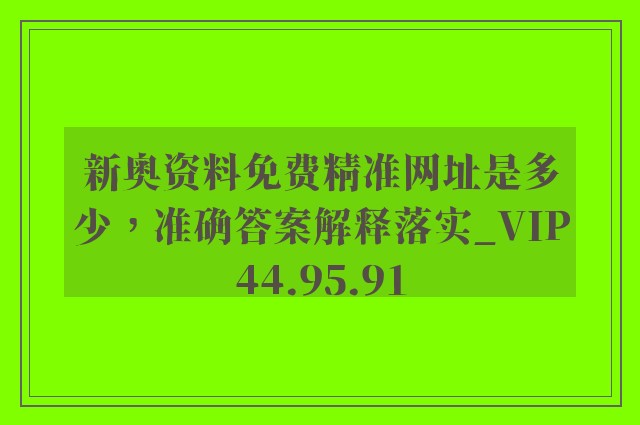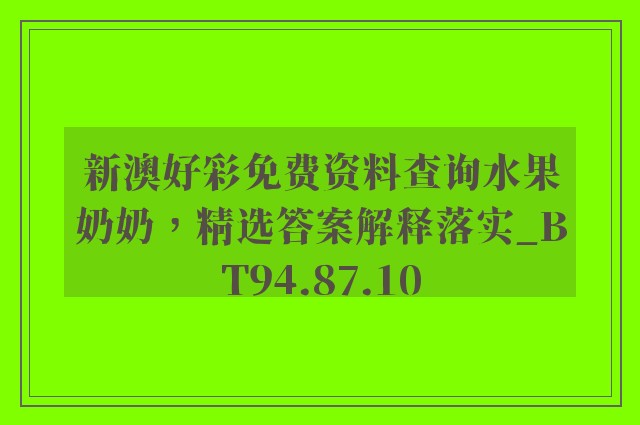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历史上有哪些横空出世的人后来却又消息全无不为人所知?」回答里有人写到,「李阳,坏飞行员,《李献计历险记》的作者,现已成谜」。
这条回答写于2015年,其中提到的《李献计历险记》是李阳的第一部作品,2009年制作的一部20分钟的动画短片。它的诞生很符合人们对天才横空出世的想象:当时李阳在一家游戏公司制作宣传动画,《李献计历险记》是他因为电脑太旧,没法玩想玩的游戏,做着取乐的。拖拖拉拉做了两年,几次差点夭折,最后为了赚北影一个奖项的30万奖金,才终于做完。这部短片并未获奖,却出乎意料地成为那一时期互联网现象级的作品,一夜爆红,甚至在之后的许多年里被多次翻拍。
在外界看来,这部片子改变了李阳的命运。他进入了一家知名影视公司,在当年的采访里,这家影视公司的计划是,「将这个有些才华但原本身处电影圈外的年轻人培养成一名新生代青年导演。」四年后,他导演的第一部真人电影《坏未来》上线,虽然仍是一部短片,却也再次印证了李阳的才华。公开消息里,《坏未来》之后,他已经开始准备下一部长片电影。
但2014年开始,互联网上就再也没有李阳的音讯。《从21世纪安全撤离》的豆瓣条目在2016年就被创立,这之后的八年,几乎每一年都有人在豆瓣短评里留言:李阳,告诉我你在干嘛?中间也不停传出电影即将开机的消息,但每次都没有下文。
——直到10年过去。这10年,李阳经历了剧本因为没人看懂而被搁置,又被发掘,项目重新启动,资金进来、断裂,又花了三年做后期,电影终于在这个夏天要跟大家见面。



《从21世纪安全撤离》

李阳与张若昀

电影《从21世纪安全撤离》中的三个少年
《从21世纪安全撤离》是一个写于10年前的故事,三个好朋友从18岁的身体里穿越到38岁,拯救这个让他们无比失望的世界。主人公和李阳同龄:生于1981年,18岁,正是1999年,一个末日传言带来的终结感和「千禧年」带来的期待感交织的年份,旧的世界已然崩塌,新的秩序尚未确立。在那个年份,18岁的主人公们满是不平,又满是期待,对着世界呼喊,「不要变坏」。
片子已经点映,收获了一些好评,也收到了一些争议。它并不是一个常规的靠情节驱动的电影,在某些地方,你会看出李阳在讲故事上的明显的短板,但一种珍贵的真挚的气息弥散其中。
一个极为炎热的午后,《人物》作者在北京见到了李阳。他戴着眼镜,扎着一个丸子头,就像他自己形容的那样,他说话「语无伦次,颠三倒四,永远抓不住重点」,但这场谈话的每一分钟,都令人意识到,他在电影里设计的每句台词都在讲他自己,讲他对未来「无端的自满和绝望」。他提到最多的词是「失落」,不管是这部电影,还是他过去的几十年,「失落」都是其中最为强烈的情绪,它关于李阳自己,也关于80后这个人群。
我们见面的会议室很大,某个角度看,像高中的教室,烈日透过玻璃显得温和几分,打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很难说时间在李阳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他的片子还和10年前一样中二、热血、悲伤。他讲述着这些年的经历,成长的感受,以及衰老带来的精神和身体上的失落,毫不掩饰,甚至有些勇敢。
关于这部片子,关于李阳过去10年到底在做什么,以下是他的讲述:
文|吕蓓卡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
2014年,我接到一个项目,当时是一个命题作文,讲三个小孩很爱唱歌,长大后一个去当理发师,一个去开出租,另一个去送外卖,忘了小时候爱唱歌的梦想,突然市面上有一个歌唱比赛,他们就重燃对音乐的热爱,得了大奖。看完我说这太像《老男孩》了,对方就说,你觉得这个剧本不行,你行你上呗。我就开始动手改。
项目有几个固定的元素,主角是三个从小到大的好朋友,热血的青春,光明的结尾。那时候青春片很流行。但我有点焦虑,我身边找不来三个好朋友。我在交朋友、维持长久友情这件事上努力过,但都失败了。那个时候我正好有点抑郁症。抑郁症最明显的三个表现,第一个是对未来没有期待,第二个是不会向他人求助,第三个是对自己没有正确认知,就凑了三个人,安到这个故事里。
王炸就是对未来没有期待。他很讨厌去未来,时间只会夺走他宝贵的东西。他小时候背着一个巨大的包,他所有宝贵的东西都在这里,一打开里面有猫,有鸟,有他喜欢的玩具,还有他爸妈的骨灰盒。他之所以把这个包背在身上,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太容易失去了。所以当王炸长大,突然觉得身上很轻,再一看小时候那个大包,变成了一个小斜挎包挂在身上,他就都明白了,时间又把我那些东西夺走了。
诚勇就是不会向别人求救。他出了麻烦,就自己把困难都背下来,跟所有人分别。这老话讲特爷们儿,有担当,你不想让别人跟你一样受苦。但当我真正经历痛苦的时候,发现一点都不爷们儿。我会逃避其他人,但目的不是保护他们,是因为我很害怕他们对我失望,离我而去,那个场面很难堪,我才知道,那样的分离其实是一种自私和懦弱。
泡泡就是对自我没有正确的认知。因为他老遭受校园霸凌,就用帽衫把自己包裹起来。他想要模仿诚勇,穿一样的牛仔服,打相同的双响指,越活越像诚勇,但他自己是没有意识到的。
我那时候对自己也挺没有正确认识的。有次坐公交汽车去芳草地,我跟人发生了冲突,我心想,你等着吧。公交车门那儿有个台阶,他站在台阶下面,我站在台阶上面,我就想车门一开我一抬腿就能踢到他。
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一伙人。我踢完他就往下跑,结果发现自己跑得很慢。冬天,三人在雪地里把我打了一顿。我躺在雪地里看着下雪的天,就发现对自己没有正确的认知,原来我成了一个跑不掉的人。
那几年我真的对自己挺失望的。接连跟女朋友分手,《李献计历险记》的时候我还挺相信那些台词,但慢慢发现自己不会像李献计那么执着。感情这个事儿好像需要巨大的生命能量去燃烧才能延续,但人类没法那么长时间地燃烧,所以爱情本身非常短暂。我就很失落。
那种失落还包含生理上的衰老。我有时候会梦到自己是一高中生,在放杂物的体育间偷偷抽烟,突然门口钥匙一响,进来一女孩,她有好多麻烦,我梦里边就拍胸脯说我都能给你解决了,硬着头皮奔赴别人要揍我的现场。
做梦到这儿我会醒过来,有几分钟我回不到当下的年纪,还会停留在梦里那个身份,慢慢看着天花板,然后知道,噢,我已经不是在学校宿舍里了,也慢慢感受到自己身体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好,噢,我现在变成一中年人了;慢慢中年的记忆回到身体里,噢,我现在面临那么多糟心事儿。身体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我再也回不到那个赤诚的时候。
让我失望的,还有一些我没办法接受的狡猾。有年大年初三晚上,我出去倒垃圾,我们家周围好多酒吧,就看胡同里走出来一男一女。女的走前头穿一高跟鞋,下雪地很滑,男的在后面推她,她走路就往前一摔一摔的。我心想那男的可能喝酒了,就冲他喊,「差不多得了!」喊完就后悔了,我心说完蛋,他可能一听我是外地的,让我滚。
我不想滚。我把垃圾放地上往他那儿走,一边走一边打量那个人的身形,我比他高,比他宽一点,没准能打赢。我上去就把他推倒,骑他身上想打他,结果那女孩在后面拿高跟鞋踢我后腰,又痒又酸,我一拳打到水泥地上,整个手破了。我就觉得她可能也不需要人帮她,就灰溜溜回家了。
后来俩人把我告了。我说他先动的手。结果一调监控,我就看我自个儿摇头晃脑的,上去「咣」把人男的推倒了。撒谎当场就被揭穿了。完了让我赔3000块医药费,我说嗨,认识都是缘分,赔1800还吉利,大过年的。就这嘴脸。我觉得我年轻时候说不了这样的话。整个事处理得让我意识到我是一挺油的中年人。有点失落,这种失落对我的打击比谎言当场被揭穿还要大。
那几年我也试图维持过友情。有个哥们儿,我跟他共同经历过学生时期几乎所有的痛苦,工作以后,我们做的方向很不一样,就发现每次见面聊天话题越来越少。最明显的是我们都没法在对方家过夜了。以前我们把对方家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一定是成宿成宿熬夜、在对方家住着那种。长大以后就很少了。
有一回吃烤串的时候,他就说,这回烤串儿咱别吃完了,这回话题也别聊完了,下回比如隔半年再见的时候,咱俩再点这盘菜,接着聊这话题。就像现在存了一个盘,半年后再读盘,继续上次的进度,那是不是就能对抗时间?
可能这样的努力太文艺了,没几回就失败了。也可能因为我们都变老,就羞于这样的尝试了。也可能是工作了没体力那么消耗,或者觉得那些玩乐的事情不值得了。反正就很希望这东西别结束,情谊别消散,但现实显然不是这样的。
我有次听一个播客,一帮人说话跟我小时候特像,互相热爱,又互相辱骂那种劲儿。我一下想到我年轻时候,我也曾经那样过,我还能那样吗?打开通讯录一看,已经没有人可以跟我这样讲话了。我没有这样的朋友了。就是一转眼的事儿。
还有一位朋友,是一漫画家,我们俩原来在一个广告公司上班。他有一次从单位离职,很长时间没有什么工作,也没有什么收入。有一天他突然很想去天津,去一个工作室做签约漫画家。
我那时候还在上班,有工资,我俩见面我说请他吃饭,但正好到月底,我手头没什么钱,我们就去了香河肉饼,8块钱一张肉饼,路边特脏的一小店,灯也不是特亮。我们面对面坐着,他突然就说要去天津,想管我借钱。其实借的一点都不多,就1000块钱。
我就脱口而出,没什么问题,但再一想,我卡上都未必有1000块钱,就一下僵到那儿了。我小时候没受过这屈,一好朋友请你帮忙,你自己卡在这儿。我坐着半天没说话,心里边跟自己说,你真是有多大本事交多少朋友吧。
我当时对自己非常失望。我跟小时候想象的自己完全不一样。比如我以为我会帮人解决麻烦,结果1000块钱就费劲吧啦。这件事给我震动特别大,就没办法再推心置腹地去交朋友。因为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不让人失望的人,我太害怕面对大家的失落,所以虽然我很想挤进人群,但我一直没那么做。我是一浑身毛病的人,我自己看自己都讨厌。
他去天津以后,我也跟当时的女朋友分手了。分得不太开心吧,我这穷毛病又上来了,不想跟那时候所有朋友联系,因为大家都认识那女孩。我跟他们就都不讲话,都断绝联系。前阵子我看到,他的漫画已经被改编了,而我跟这个哥们,20年没见。
现在想想,世界就是一场幻觉。
剧本2015年写完,停滞了很长时间。因为大家都说看不懂,就没有修改,没有推进,因为没有人愿意拍这个电影。中间有三四年,我都有点把这个事忘了。到2019年剧本(《从21世纪安全撤离》)被重新拿出来之前,我都在做一些策划的工作,解决生存的问题。
我以前看一电影叫《囚徒》,同天还看了另一个片子,跟《囚徒》特别像。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好莱坞会一个点子出现在两个电影里,直到我做策划,这策划会我想了一个点子,讲了一天倍儿累,晚上还有一策划会,我就偷懒,把上午的点子再讲一遍。我一下就理解了,那可能是好莱坞有跟我一样混事儿的人。
2019年前后,剧本所有权的公司想让张若昀演一个谍战电视剧,但他很排斥演相似的角色,公司觉得好不容易牵上线,再看看还有什么储备项目,就想到这个剧本,是写往中年去的年轻人,拿给他看,他看懂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方面觉得开心,你瞧,我不是个垃圾;另一方面我心想,那是2014年的故事,是不是五年过去了,本来新鲜的东西大家觉得不新鲜了,岁月让这个东西变得好懂了?
也可能张若昀跟我的知识结构有点像,他很开心,想演王炸。我俩加上微信,他上来第一句话就说,我是王炸本炸。当时还是那样的流行语。按理说我看到这句话应该高兴,但我高兴不起来。我觉得你怎么会喜欢这样古怪的故事呢?你是不是在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必须得这么给我发一微信?
这个项目,主演进来之后,尤其张若昀是《庆余年》的主演,它就变得很顺利。我就想,不能完全由着我的性子来。王炸这个角色我一开始想的是一个完全傻乐、没心没肺的人物。我第一次见张若昀他比现在胖,我就说了一句,王炸应该特别瘦,他的人物特点决定他每天吃不饱,还跑来跑去,所以不能是一个看起来营养很充分的人。聊到后来,若昀说他对这个角色有非常深的认识,深到我不用再向他提供这个角色的特点。
听完他说这话,我不信。之后疫情各种,我俩好久没见,再见到他,他突然就变成特别瘦的一个人。我心里特别难过,因为他瘦了以后有一点忧伤。我问他你怎么了,他说没什么,也没跟我细讲。
我心想,王炸应该是一傻乐的人,你怎么能忧伤呢?后来拍那场在桥洞底下的戏,王炸不想诚勇再继续糟糕的生活,诚勇跟他讲,你赶紧走,假装不认识我。拍的时候,张若昀突然用比宋洋更大的声音喊,「我没法不认识你。」那是一个非常忧伤的人会讲的话。
那一瞬间我在想,我为什么会变得没有朋友,因为我不会对朋友讲我的需求。但王炸会非常令人心碎地讲出这样的话,哪怕他知道这话说出来也没用。所以那是个非常恰如其分的忧伤的呐喊。我突然觉得我不能一意孤行,把王炸塑造成一个傻了吧唧、完全不会哭的角色,张若昀塑造角色的方式比我剧本里写的要丰富特别多。
他是非常有赤子之心,没有被熄灭的那种人。那是我向往的成年人的形象,我很努力想要变成那个没有被熄灭的人,但事实不是这样。
有一场戏是王炸喜欢刘连枝,但他心里面是个18岁的少年,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太过直接导致刘连枝经常拒绝他。但他很心疼刘连枝,他就跟刘连枝说我不想让你在生活里面犯糊涂。刘连枝说,谁活着不是装糊涂。王炸就回答说我不是啊。刘连枝就说因为你没长大,这时候王炸说,那你也不是什么大人。
这场戏本来设计得很简单,但张若昀突然跳出了分镜,把手里一捧花举起来,杵到刘连枝面前,喊了那么一句话。我很喜欢他的这个设计,好像这捧花是一个灵魂契约的东西,如果你接受了这个花束,我们就会产生比男女之情更牢不可破的情感。因为他们俩是同类,像蝙蝠群里面混进的两只海鸥,他们两个人能看到太阳和海潮的起落,他们说的话只有彼此才能听得懂。
如果刘连枝接受了这个契约,王炸就会不顾一切跟她一起对抗那个可怕的世界。当时张若昀的念白和表演形成的气场,让我非常坚信这是一个赤子之心从来没有被浇灭的家伙。那是我非常向往的状态,所以我现场非常嫉妒,嫉妒坏了。我就扭曲,歇斯底里通过耳机跟钟楚曦喊,别听王炸的,把那个门关上,用那个门缝把花挤碎!
刘连枝就特别矫健地把那个道具花挤碎了。
之前做动画,都是我一个人的工作,当导演要跟很多人合作,对我来说很难,对和我合作的演员来说,可能也很难。
张若昀和钟楚曦第一次来,是拍摄一场夜戏。我太想把这个戏讲好,太想假装自己是个特专业的人,就引经据典讲了半天。我觉得我说得富有文采,结果一开机,俩人跟春晚小品似的演了个特喜剧的东西。
我完全绝望了,我说我讲的不是这个,就恢复语无伦次的状态,过去跟人家说春晚度能不能再降低60%?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词,「春晚度」,这是一度量衡吗?但我现场只能说这样的词。但他们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意思,第二条就是完全相反的表演方式。我后来看过陈凯歌拍摄现场的花絮,怎么跟演员讲戏,那是我追求的状态,但我发现很难,我不是那样的导演。
这是我第一回拍长片,我甚至没有概念70天到底能拍多少东西,就写了很多场戏,分镜头画了三千多个,平均2秒左右一个。我有点阅读障碍,所以没法看很复杂的剧情。尤其外语的喜剧,翻译很长一段字幕,那个字幕演完我还没读完,旁边的人都在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笑。我只能看动作片,因为对话很少,看他们叮咣打得我就很开心。到自己能拍片儿,就觉得人家都是买票来的,这帮人里保不齐有像我这样阅读很困难的人,不能让他们白来。
开筹备会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拍不完。我跟个纣王似的说,怎么能拍不完?必须得拍。时间久了,发现确实没有希望拍完,剧本删了五分之一。后边又遇到资金链突然断的情况,又有一部分戏拍不了。
在拍摄当中,资金链断是致命的,大家都有档期,哪怕现场茶水都有档期,如果不拍就意味着丧失再拍的机会。那个时候有点难过,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没拿钱,还在帮我一块做这个事。
有一天出工,只剩下摄影部门,移动组都没有,拍动作戏甚至连轨道都没有,吊威亚也没有,就替身在。结果早上起来,演员那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宋洋到现场了。那天通告里本来不应该有他,我以为我听错了,就没管这事。一直到中午,我正吃饭呢,一抬头眼前站一血人,宋洋化着全妆来了。
有场戏他被打得特惨,浑身是血。他就那么待了一上午。读剧本时他发现这儿应该有完整的打戏,他知道动作戏应该有多少量才能完整塑造这个角色,不然不成立,他就满脸鲜血地质问我,为什么你没有发通告给我?
我心里边非常感动。但哪怕这样,能弥补的东西也有限。因为很多打戏是所有人都参与的,得有群感。我就只能改剧本,比如打架,突然俩小孩在这儿开始说评书了,把打斗过程叙述出来。这样就不用移动组,一台摄影机就可以拍完。
我是那种人,当我的设想没法成型的时候,我会很生气,攻击性的那一面就会出现。拍摄过程中,有一次制片主任把地陪给得罪了,导致我们之前看好的景提前一天跟你说不能用了。我和美术凌晨2点出去找新的景,找到了野外的一条路,我心想这路总不能给我破坏了吧,它是一条天然的路。结果第二天去拍,发现边上有俩挖掘机把那路挖成一大坑,完全没法拍。
我就很生气这事,演员来了还得假装这景就是我想改的,还跟他们讲戏,说这比以前的设计要好。张若昀后来发现,我怎么每次讲戏都特心虚,问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也是第一次来这景儿。
大家都包容我,就没有让那个攻击性的我膨胀起来。有一个医院的场景,我拍的方法特庸俗,一摄像机拍车轱辘,一摄像机拍天花板好多日光灯,假装推车推特快往前走。我看好一个医院,仅仅是因为屋顶有连贯的日光灯。临时有变化,不能在那儿拍了,要去一个没有日光灯的医院,给我吓傻了,我说这怎么拍,医院我只会那个机位,这一变我唯一的机位都没有了。
我那个攻击性马上要出来说,我就要在这儿拍,再一看,上午拍下雪戏的机器还在,我说要不然在屋里下雪吧。把灯都关了,一下雪就看不清医院的墙跟房顶了。
现场所有人就突然特别配合我。这是一个混招吧,哪有拍不了日光灯,就让室内下雪的?但大家突然都特别配合我顺利拍完那个镜头。那是我一个月里边最喜欢的镜头。我好像找到了跟那个失落对抗的方式,慢慢会去想办法解决问题。
到了做后期的阶段,又有一些特效镜头也执行不了,我久违的攻击性人格又出现了。那天特效指导突然跟我说,6场特效要删掉4场,因为没有钱。我说解决方案是什么,他说解决方案就是删掉。我说可是这有叙事的功能,他说没有办法,要么就开天窗。这两个是相同的答案,我就那个嘴脸,我说你删就删吧,摔门而出。
我又没地儿去,就去了趟厕所,在厕所里我就发现如果我说「删就删」,那就真的删掉了,它就是一个连不上的故事。人家陪我这么久,难道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又回去,坐下来想办法。《坏未来》的时候就没钱去做特效,用了动画。这次也是,自己再画一点,把叙事的部分补上了。
我想捍卫这个故事,也不是捍卫,我本身人格没那么高尚,而是其他人对这事儿的付出多了,我会有那个情绪在。有一些戏我很想坚持,不想拿掉,因为我会想起主创那帮人。我们去南方拍的时候是2020年,据说是最冷的冬天,拍的是暑假,还人工降雨,山里面一帮人冻得不行,摄影组所有人都在泥泞的地里咳嗽。我想起那一幕,就觉得大家一块跟我浪费了70天,我没有权利让这个东西变成泡影。
我很感谢这部片子的监制王红卫。他总是适时地来安慰我。剧本写的时候有一些部分,我写得很低落,但一个成熟的剧作,有一趴低落就够了,后面就不要再让主人公往更深处跌落。还是王红卫来鼓励我,说要保留下这些部分,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那么欣欣向荣。结果被他说中了。
这部片子从2020年底开始拍,拍了70天,2021年初拍完。从拍完到剪辑完又是三四年的时间。中间这些年,我过得很狼狈。
以前别人找我去看片,他辛辛苦苦拍完一片儿,问我说你觉得这片好吗?我说用IMDB的标准打分5.8吧。我当时就是攻击性人格,留一寸头,找茬那劲儿。到这岁数我很后悔,我干嘛攻击人家。因为我也吃过那苦,就发现我没有必要那么刻薄去跟人讲话。有的导演可以非常圆融地接纳别人的攻击和恶意,对这个职位来说,那是一个必备的技能,但我需要分很多精力去消化那个攻击和恶意。
我也没有正规学过导演,对导演水平的高低没有特别清晰的概念,没有那么牢不可破的标准去判断哪种表演方式是更好的。我只会这种讲述方式。尤其遇到资金不顺利的时候,我无能为力,我发现我很久没有更新自己后期的知识。我很后悔,如果我一直保持旺盛的学习精力,就能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说这事我一人就办了。我很愿意扮演那个英雄角色,但我性格导致我没法那么英勇。整个事卡在这里下不去,特别无力。
他们说我是一讲科幻故事的人。其实我根本不是,我是一懦弱的人。我不敢讲自己的故事,又鼠目寸光,只熟悉自己的故事,但又没胆量用第一人称去讲我熟悉的故事,就得用一个假装科幻的外壳,这样套上就没人知道这是我的事了。也许我经过刻苦努力的学习,掌握了用技巧讲故事的方式,就不用老讲我自个的故事了。
你问我这些年行业的变化,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下行的速度快于行业下行的速度,生活里边有一堆焦头烂额的事,所以我就没功夫搭理这个。
我小时候看《生化危机》的游戏制作人三上真司说,一个想法诞生的时候,最后只能剩60%。我当时还不信,这次就明白了。《从21世纪安全撤离》最后大概就是剩60%左右。也可能是因为我经验不足,才导致这个结果。
我在片子里拍的那种对未来的幻想,好像源自于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就会对未来有无端的绝望,和没有任何理由的自满。
我以前家里条件比较好,那提供了一种对生活的安全感。初中我练过短跑,当时我想,如果能评上国家二级运动员,这辈子就不用愁了。我那时候不愿意学习,很愿意去台球厅或者街机厅玩。
后来短跑没练出来,我要考高中,我爸说你不用太担心,他知道我学习不好,他说高中是积累人脉、形成世界观的时候,我考得再不好也会陪我想办法。
我就相信了,考特差。忘了具体多少分了,反正正好是满分的一半。我跟好多同学去看榜,我还在那儿高兴呢,我说你瞧,正好一半,高兴了一路。跟《活着》里富贵那劲儿似的,惹了多大祸都嘻嘻哈哈的。回家跟我爸说这成绩,结果,我爸这辈子没生过那么大气,没见过这么低的分。他说你给我滚,他完全不想救我。
我就去县城上学,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不吃饭就开始跑步,跑完步在餐厅里15分钟吃完早饭,去早自习,大家都坐在那儿大声朗读,你会看到一个人突然特别恐惧地弹起来就往教室外面跑。因为他想起自己牙刷的朝向跟别人不一样。
我爸特别想给我颜色看看,不能让我变成一个混蛋嘛,高中三年,我跟我爸接触很少,一个月可能就见一面。
高考那年,我爸意外去世了。正好是1999年。那会儿流行「世界末日」的说法,我特别爱跟同学说风凉话,我说你们还学什么劲儿啊,高考那天就末日了,大家一块玩儿完。结果他们没有末日,就我一人末日了。
我爸去世后,我妈找到了他的日记。很多年以后我妈跟我读,里边写满了对我的失望,说他一辈子刚正不阿,我怎么会这样?还说我今天又干了一个什么不好的事,已经多少次了,他觉得我未来没有希望,怎样完全活成了他相反的样子。我特别想反驳,我不是这样人,我现在不这样了,也有工作,跟人家也都客客气气的,再一想,我没有那个机会反驳了。
后来我做一梦,「李献计」之后吧,我爸还是特年轻时候的样子,横眉冷对那个劲儿,坐在床头。我已经开始衰老,看着我爸特别愁苦,但是很帅气,我说你愁什么,你这么帅。我爸说工作没干好,我说这人死了还要工作啊,是什么工作?他说那窟窿没堵上。我就安慰他,说我没有小时候那么糟了。因为过于想自我表现,我就没有追问他窟窿是什么东西。
后来我醒过来,想到他既然提了窟窿,那一定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窟窿。那世界上最有名的窟窿,就是南极上空臭氧层破的窟窿。大气层是保护地球上人类呼吸和生活的基础硬件,我就想,原来人死以后没有去天堂,而是回归这个星球,变成大气层了,继续保护自己在乎的人。原来他去那儿了。
经历这些,我生活里比较大的变化是安全感没了,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的。以前家里还能保护我,长大以后就不能那样。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德国念书。那时候有两个流行的专业,一个国际贸易,一个计算机。计算机可以打游戏,我就选了计算机,其实也没好好学习,拿着申根签证满欧洲玩。没毕业就回国了,去北影动画学院做了一年进修生。读完就在广告公司和游戏公司找了个班上。2007年,当时因为电脑很旧,玩不了游戏,就找了一个画漫画时候编的故事开始做动画,就是《李献计历险记》。后来买了新电脑,我就每天打游戏,很长时间一笔动画都没动,差点就半途而废了,直到2009年才做完。
《李献计历险记》做完之后,我就进入了影视行业。我生活上倒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可能我已经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巨大人生下坡路,我会把一些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也许是我哪做地不好,也许是我犯了一些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副作用:我会觉得自己配不上好东西。那会儿明明人家特真诚给我一个好处,比如一些工作机会,但我就得把这事强行推走,因为我觉得我配不上,我觉得自己是个一定会搞砸的家伙。
后来为了还人情,我写了两个剧本,一个是《坏未来》的前身,一个是关于西游记的故事,跟人家说,我没钱赔您这项目,这剧本您收着。结果人家说,这俩剧本我都没看懂。
正好优酷来找我,问要不要拍个短片,公司就把其中一个拿出来。优酷看完之后,说只有50万,那个剧本属于长片,得缩减,最后就成了《坏未来》。
那时候我完全不专业,整个场面都特别荒唐,拍摄现场拿一棍在地上画,哪些能拍,哪些不能拍。比如要拍一个场景,应该远中近特写这个顺序来。我不懂,第一个远景拍完,我让远景、灯光都撤了,下面拍特写。到第三个镜头回到远景,大家重新布回来。一开始人家以为我是王家卫,时间久了一看,诶,原来是不懂。就每天都给人弄得特别疲劳。
我那时候留的圆寸。其实你要观察一个人对暴力到底有没有敏感性,就看他留的发型。圆寸打架时候对方抓不住你头发,你就不会受制于他。我那时候很敏感,老感觉剧组人要抽我一顿,每天在家里练俯卧撑,就想别到时候揍我完全不能还手。
所以那个混乱的场面我非常知道。故事变成最后那样我也非常知道,因为没有按计划拍完。我也没有能力控制后期,只好加入大量的旁白让故事完整。我甚至都没有脸去找段博文录旁白,因为我很喜欢他,我不想在他面前表现出我是一不靠谱的人,不想让他知道这个事我搞砸了,最后你听到里面好多旁白是我学段博文讲话。
无心插柳,这个片子的反响很好,有人说喜欢,但我心里很清楚,您这跟我客气了。
拍完《李献计历险记》之后的那几年,我也对未来有过一些特别错误的期待,我一度觉得我在用主流的方式讲故事,我可以随便讲故事。
那会还是web1.0到web2.0的时代,有一些采访,遇见的人会跟我说,我喜欢你的故事。这是我之前没有过的。我从小就喜欢胡说八道,故事讲了10分钟,大家纷纷散场,听不下去那种。所以当有人来跟我说他喜欢这个故事,这样的人超过10个,我就会以为,哦,我这是主流的故事。
因为那时候一旦有讲青春的故事和电影我都很难融入,大家都特别干净,有特别单纯、光鲜的少年时期,但我分明记得我的少年时期特别不堪,做的事好像也不那么光明磊落。《李献计》被那么多人看到,我一度以为这么不堪的少年是可以成为主流的。
那时,我接受采访时说起,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S·H·E的歌迷,和其他歌迷一起去看她们的演唱会,举着荧光棒,大喊她们仨的名字,中文的英文的,我全知道。感觉特别好,因为当你成为一个主流的人,有了主流的喜好,你会发现自己可以迅速收集到关于自己喜欢的人的一切信息,而且多了很多朋友,无论说什么,他们全都能明白。你会觉得特别幸福,因为得到那些东西很容易,周围的人也全都理解你了。所以,当你变成一个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人时,你会发现,成为一个主流的人,是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法,因为你拥有了自己的精神支柱。
也许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和本领融入主流,但现在发现自己是一固执的家伙。我有点分不清,我到底是过于固执以至于没法融入人群,还是我在说服自己,不融入人群是一好事。
但我其实挺想讲主流的故事,我想讲一个大家理解起来完全没有障碍、不需要费劲的故事,但我从小说话颠三倒四,没有重点。我费尽力气,哪怕尝试讲一个青春的片,都得让人转一下才能知道我在讲什么。
生活上,我好像也没办法融入那个主流。因为我酒精过敏。我最近去一个局上,大家都不怎么熟悉,但能一块儿在那个局里互相敞开心扉。哪怕是有点拘着的人,稍微喝点酒,下半夜也都说成一团。但我没法靠喝酒融入这样的局面。还有酒量好的人过来跟我讲,看你挺贼的,我喝成这样你一滴都不沾呐。
现在还有抖音的粉丝数之类的硬性标准,告诉你什么是主流。显然,不是我想变成主流就可以变成的。打破对主流的幻想其实是一个漫长且痛苦的过程。是不是80后好多人现在还是在主流啊?只是我不小心掉队了。现在我能自己安慰自己,当我远离主流的时候,我跟不上21世纪的主流,还能跟上90年代的主流。
最近《从21世纪安全撤离》片子做完,还有一些人跟我讲,他们没法理解这个故事。电影是商品,对我来讲,我已经尽我可能全心全意为大家、为观众着想,我尽力了。
我把片子里的时间设定在1999年,那一年片子里三个男孩18岁,我也18岁。片子里用了一些苏联音乐,我小时候,正是苏联歌曲大行其道的时候。
这些音乐很多放在了诚勇爸爸的段落,他是个下岗工人,家里有一面墙都是坏掉的电视机,另一面墙是金鱼,这么设置是想表达,普通下岗工人会以小组为单位开一饭店,大家互相支撑、互相帮助这么走下去,但诚勇他爸是个部门组长,遇到困难不会向任何人求助,下岗以后就说用我这手艺给人修电视,但重工跟轻工不一样,电视都给人修坏了,他又不好意思管人要钱,电视就堆在家里。
另一面墙的金鱼,是他不会修电视,就卖金鱼去了。但他是一工人阶级,又不会叫卖,金鱼就都砸手里,最后变成一个靠卖字为生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被时代抛弃的人。
他非常坚强,从来没哭过,那年春节晚会第一次哭,因为刘欢唱了一个《从头再来》。「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他一下就哭了。钢铁在融化,但还是会变成钢铁,还是会很痛苦,你怎么能轻描淡写地讲,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在电影最初的设计里,三个男孩一开始打架的火车道,是一个钢铁厂。诚勇被拖下水的时候,水底有一个沉底的佛头,代表「文革」时期被推倒的传统文化。但在1999年,钢铁厂也变得破败,新的世纪要到来,过去那一套也要瓦解。
1999年世界的变化特别有趣。要跨入21世纪,公安系统的服装从绿色换成了蓝色,以前都是布的肩章,换成铁的肩章,人民币也换了,好像整个旧世界都在消失。可能更早一点像60后、50后,他们存在的痕迹就一样一样都消失了,有点像我今天的境遇。那是一个旧的标志批量死去的年代,「世界末日」的说法也在流传。
电影的最后,还是1999年,小孩骑着自行车远去,那看起来是一个美好结局,但他们立刻要面对的是身体里边的毒药每天还会再分泌出一点,今天如果不去对抗,他就会死掉。他们同样要面临残酷的现实,会不可避免地堕入到新的中年人的麻烦里。
这种失落好像是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都会有的。我们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在当时社会就有讨论,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一代。因为独生子女家里娇生惯养,但成功都来自于苦难,那时候是那样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果然没有做出什么让人津津乐道的创举,那种失落就已经成为定论了。
201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世界末日的说法。那时候我奶奶还活着,她是特别虔诚的基督教徒。2012年之前催我结婚,但那天就偷偷把我拉到一边说,千万别结婚,我给你说个事你别出去说,圣经上说了,2012年世纪末日。
我说人电影都拍完了。当时我已经有些人生困境出现了。我为什么不结婚,不生小孩,因为我很害怕孩子长到十来岁的时候问我相同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没有人是快乐的,我没法回答他。我妈也没回答我类似的问题。那一年,我觉得有一些感情关系无以为继,如果有一场末日到来,我可能会高兴。我没想好2012年如果我们都活下来,我怎么面对那些问题。有天在家里想这事,我妈就突然附和我说,她也不知道。我就发现,原来她也不是那么快乐。
到现在,我身边的同龄人都「大富大贵」了吧。以前广告公司的同事都出来开公司,都挺快乐的。我也还行。但我那个最好的哥们不太开心,他是一特别高瞻远瞩、有预见性的人。他能考虑到很多年以后的痛苦。他结婚那年就突然跟我说他不想结婚,但是迫于生活的压力他必须完成一个婚姻。
前两年我们再见,他说如果让他再过一遍人生的话,他会坚定不结婚。过去我不会想到他有一天跟我讲他不想要孩子,不想要结婚,因为我觉得他会过那种所有人都羡慕的生活。又过两年,疫情这些阶段他压力变得更大,就滑向更加难过的自我中去了。今年过年我想找他,他完全不理我,叫都叫不出来。我猜他可能连自己都不喜欢了。
对自己失望这事我很有经验,我其实很想跟他切磋一下。